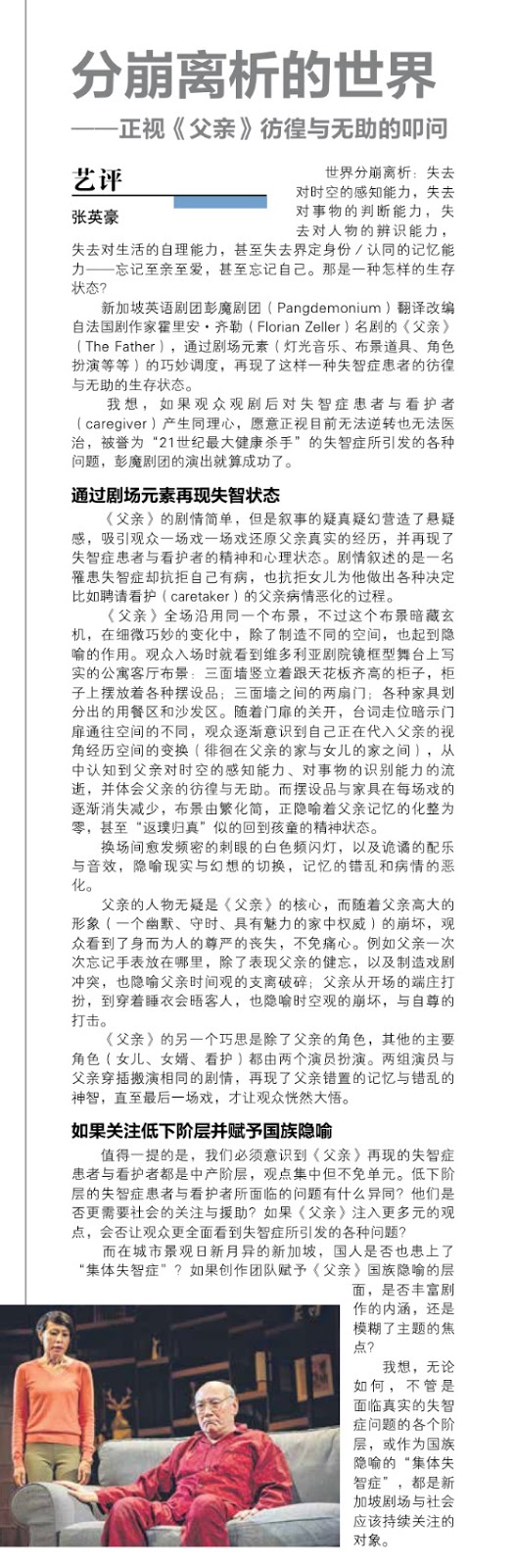剧评:爱因与斯坦

倾听《爱因与斯坦》的提问 文:张英豪 中国昆曲与西方音乐剧,通过爱因斯坦(科学),会在停车场(现代)内,碰撞出什么戏剧效果(剧场)? 答案是相对论。 从概念层面切入解读 2018华艺节,“避难阶段”剧团在滨海艺术中心地下停车场,呈献特定场域演出《爱因与斯坦》(Einstein in the Carpark)。 这是一部非叙事性的剧场文本,观者如果从叙事的角度切入诠释,将会碰到理解与感受的障碍。观者或许可尝试从概念的层面切入解读。 《爱因与斯坦》的演出概念本身就充斥着戏剧张力——昆曲与音乐剧,分别代表中国与西方的艺术/文化;爱因斯坦象征与艺术/文化成对比的科学,并分裂成一体两面的人物爱因与斯坦;停车场作为现代的空间概念,被布置成非正规的表演空间。避难阶段艺术总监刘晓义领导表演者田伟鸿与张军,以及黄泽晖(声音艺术与音乐创作)与林菀雯(灯光艺术)集体创作,在执行这些概念的对话时,碰撞出怎样的效果与意义? 《爱因与斯坦》延续刘晓义这几年的作品特色——强调提问,引发观者思考。演出在刘晓义“这是一个通告”(This is an Announcement)的英语录音播放中展开,其中一句“这是一个问题”,以及场刊中《导演的话:给爱因斯坦的33个问题》,奠定了提问的基调。而提问的方式不限于问句,还包括演出希望让观者产生的各种问题意识。 借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以及剧场时空的调度,《爱因与斯坦》试图引发观者对时间与空间,对置身时空中的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,对人的存在与羁绊,产生更深刻的思考。观众在入场时拿到的观剧装备(收录演出文字文本的《这是一份翻译》,画出表演区域的停车场地图、例常的场刊,以及贴心提供的折扇和矿泉水),提供了一些解读的线索。 停车场被布置成宛若装置艺术的展厅,让观众与各种装置互动:交通锥播放着录音,或提供角度,供观者聆听与窥看;黄黑相间的警示线划分出的装置区域;水面如镜的一池浅水;一辆播放着科学理论英文录音的完好的汽车;一辆车头撞毁的破烂的汽车;墙壁上一幅科学方程式似的图表;一台破旧的钢琴;放置着发光耳机的高脚椅等等。 戏剧性在时空的涣散 可惜的是,演出整体的能量(不只是表演,还包括导演的调度,声音灯光的设计等等)无法撑起停车场偌大的空间,缺乏足够的戏剧性吸引与维持观众的注意力。这也导致观众无法对演出产生更有意义